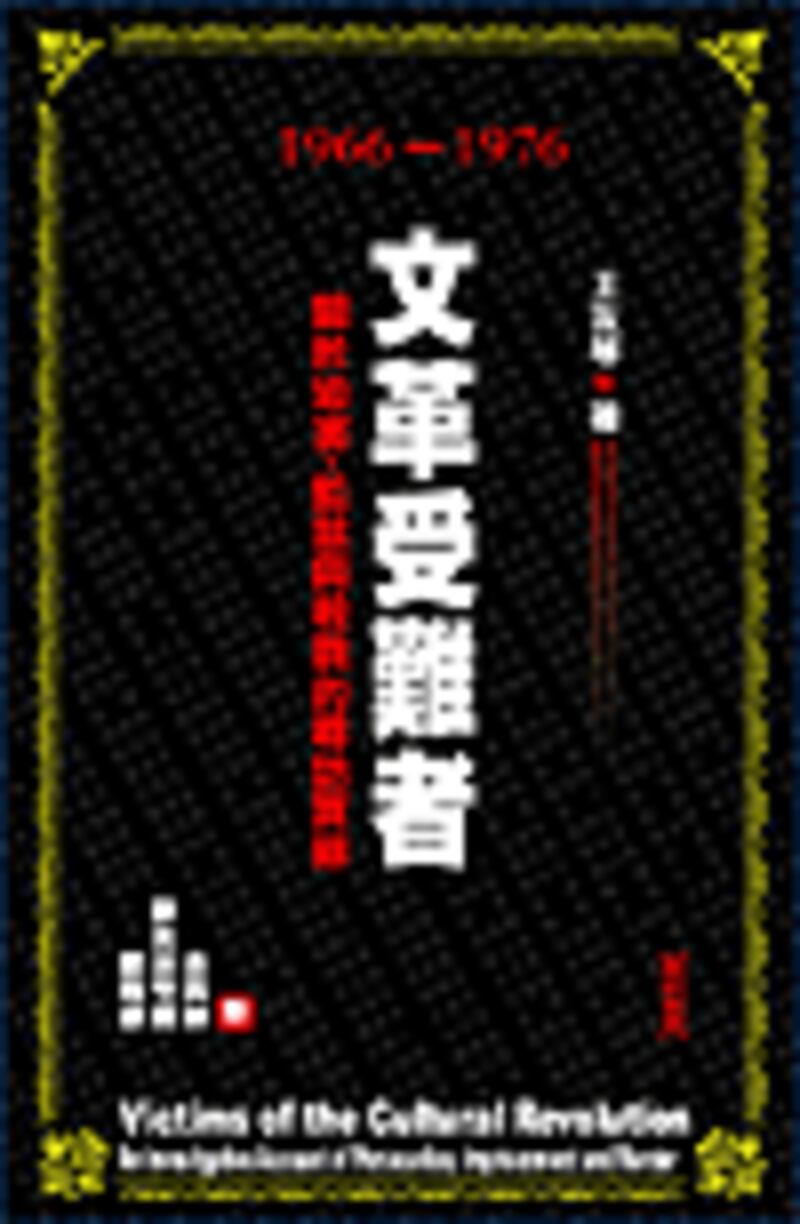
王友琴:“當然寫這些題材的書不是愉快的事情,但是文革不單單殺害這么多的人,而且還給所有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創傷,這些恐懼、對事實道德責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。很多人仍在問‘我說這些事情,會有麻煩嗎?會有監視我們談話嗎’ 。那种恐懼讓我明白,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壓迫和心理創傷有多么大。我在寫作過程中,對人生以及歷史有產生了比較深刻的認識,也認識了對個人來說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德立場。”
從80年代初開始搜集資料,到2004年5月出版《文革受難者》,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系教授,資深文革學者王友琴整整花了20多年時間在尋找文革受難者的工作上。她說,自己是本著做人的基本道德觀來獨立從事這份工作。
王友琴: “當然寫這些題材的書不是愉快的事情,但是文革不單單殺害這么多的人,而且還給所有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創傷,這些恐懼、對事實道德責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。很多人仍在問‘我說這些事情,會有麻煩嗎?會有監視我們談話嗎’ 。那种恐懼讓我明白,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壓迫和心理創傷有多么大。我在寫作過程中,對人生以及歷史有產生了比較深刻的認識,也認識了對個人來說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德立場。”
受難者家屬要承受失去親人和無法表達悲痛的雙重痛苦
王友琴透露,在她搜集資料的過程,受難者家屬所組成的一個整体形象給了她最深刻的印象,因為他們要承受失去家人以及無法表達哀悼悲痛的雙重痛苦。
王友琴: “受難者家屬受到非常非常嚴重的迫害,給他們精神造成非常大的創傷。我跟很多家屬面對面談話,他們的表情和眼神都曾經使我震惊,他們提到這些事情的時候,都非常痛苦,盡管在平常生活都已經把痛苦掩蓋,讓自己忘掉。實際上,他們心里面的悲痛是非常深重的。我覺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希望有地方記錄這事情,就像中國人几千年傳統,家里面死了人,是要修墳紀念的,因此壓制關于文革記錄的發表,也是非常殘酷的事情,因為家屬的悲痛無法得到表達。”
在中國,研究文革歷史,至今還算是一個禁忌,有關的作品,往往是點到即止,像《文革受難者》一樣赤裸裸地揭露那個年頭的丑惡和殘酷的書籍,還是少之又少的。王友琴透露,在搜集資料過程中,她曾經受到過一定的壓力和威脅。
行兇者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威脅作者
王友琴: “ (壓力)是有的。我可以告訴你,也曾經有來威脅過我的人,就是那些曾經做過暴力行為的人,他們來威脅我,甚至有意思說要來打我,也有人給我打電話,說為什么你不淡忘歷史。這也很令人震惊,在事情過去這么多年,這些人非但不道歉忏悔,反而來威脅,這是最嚴重,另外也有人說我妖魔化了紅衛兵。我也收到過這樣的信,說毛這樣作為什么不可以,殺死這些人為什么不可以?說中國就是需要秦始皇。
“在書的前言里,我說過,文革不像德國,德國在二戰后有非納粹化的過程,首先是在組織上清除了納粹分子。同時學者能夠有机會對納粹進行詳細的反省,但是這中反省在中國沒有,甚至現在還有人抱著文革的心態、甚至做法。但是大部分讀者還是愿意接受事實,如果他們以前不知道就是因為不知道,不是因為他們知道了事實,還要說,殺死這些人有什么關系。”
王友琴表示,在搜集資料以及撰寫文章的過程中,她并沒有受到官方什么壓力,但是這并不代表中國政府開放了這方面的禁區。比如說,她所主持的网上文革紀念園,就在2002年3月突然被封鎖,中國网民無法再連接到紀念園。
王友琴: “2002年3月中旬,网站忽然不通了,沒有警告也沒有通知。但是我想封鎖网站的那邊一定有机构在作這事情,其實這很令人擔心,好象他們就是老天爺一樣,是否到現在為止,我們還要像接受天气一樣來接受這些禁令?”
《文革受難者》一書,是以659名受難者的故事為骨干展開,受難者的資料很清楚,但是就絕少提到作惡者的身份。王說,她并非為了刻意回避問題。她雖然沒有在書中到底是誰造成這些罪惡,但是在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,她就作出了簡單的分析。
我們無法叫他們忏悔,但是至少要爭取權利把事實講出來
王友琴: “關于誰造成這些罪惡,我有比較基本的分析:第一,這是在毛的指揮領導鼓動下發生的,他還有具体的指示。比如說,沙坪被打死之后,她學校里面有一位副校長董光台,董光台父親是共產党早年的重要人物,他的家人于是給毛寫信,毛就毛批示把董給放了,可見毛是知道這些事情的。第二是因為有了紅衛兵的組織,如果沒有紅衛兵,情況不會發展到這樣的情況。第三是因為很多普通人人性惡的一面被煽動起來。
“對于到現在為止,這些參与坏事的人,他們不愿意承認面對這些事情,我們無法叫他們忏悔,但是至少爭取權利把事情說出來。”
各位聽眾,這一集的《文革受難者》專輯到此為止。在下一集,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出版經過,并會邀請到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、美國普林史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教授以及《文革受難者》出版人、開放雜志主編金鐘先生,同大家就這本書作出評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