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部分海内外的年轻人来说,他们怀抱著让社会进步的理想,却因为当今中国政治环境,让他们感到无力、孤独、愧疚。本台记者陈品洁访问了多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,听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。
2018年冬天的某一个夜晚,互联网上昵称为“祈翠”的中国留学生,在美国东部的宿舍里,看著网上流传的抑郁症自我检查表:“是否一直感到伤心或悲哀?”、“是否感到前景渺茫?”、“是否长期失眠或睡眠品质变差?”她不知不觉在几乎所有项目上打勾。
当时西方媒体关注美中贸易战、新疆再教育营,以及隔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。祈翠认为自己只是基于对家乡的情感,外加面临毕业后找工作的压力,导致暂时出现了抑郁症状。尽管找到合意的工作曾让她一度以为自己恢复了,但祈翠的情绪随后被国内局势不断恶化的新闻重新打回谷底。她曾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过分敏感。
从彻夜刷推到麻木
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,世界各国将矛头对准中国,同样在国内,纪录武汉封城的《方方日记》在互联网上引起回响,多名公民记者也为调查疫情真相而相继遭逮捕。
祈翠回想当时的心情,向本台说:“刚开始疫情的时候,几乎是在通宵刷推(推特)或者发微博,像强迫症一样的刷推发微博,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我只有一半的魂是在现实生活中,另外一半的魂在网上政治抑郁。这一切都被政府的胡作非为毁掉了。”
每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社会案件、当地政府的错误决策,以及随之而来的删帖炸号,都让祈翠感到愤怒沮丧。2022年2月,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枪声响起,她的政治性抑郁被推往巅峰,然后整个人麻木了。
祈翠:“政治性抑郁也会渐渐麻木吧,我已经从被愤怒冲击到必须说点什么、做点什么的状态,变成现在我意识到我可能无法改变它。按道理说,任何人都不应该长期处于政治抑郁的状态之下,但是当你身为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时,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政治抑郁,那么你要嘛是坏、要嘛是傻。”

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根本原因
祈翠不是唯一一位有政治性抑郁的人。疫情期间,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各式“抗疫科普”、“疫情下的政治性抑郁”等文章,教导民众如何纾压、调解忧郁情绪。在中国政府高压统治、严密审查之下,大部分的民众面对社会事件,趋向于做把头埋在沙漠里的鸵鸟。
这些文章没说的是,许多抱有理想的青年之所以“政治性抑郁”,是来自对于当今政府的不满,却身处高压环境自身无法改变的无力感,以及因为严格审查制度、迅速删帖封号,让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抒发却得不到回应、找不到共鸣,不仅觉得孤军奋战,更像脖子被掐著,发不出声音。
身在国内的张姓大学生说:“算是不好受,也是无奈。时常发外网、发朋友圈吐槽,会用一些阴阳怪气(的方式)。我更多是觉得无奈。”
张同学的政治抑郁来自于个人体验,他在高中期间曾经举报该校中学生的基本人权遭侵犯,而被校方打压、噤声。自此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、乃至政府体制可能有问题。
“我为了研究六四(运动),把《人民日报》从4月15号到6月4号的报道都看了一下,觉得叹息、无奈、想哭。原来当年《人民日报》真的是一家敢讲真话、为民发声的媒体,真的是群众的喉舌。”
张同学告诉本台记者,原本以为改革开放是个起点,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能带来政治局势的改革、带来民主进步,现在却发现“没对比,没伤害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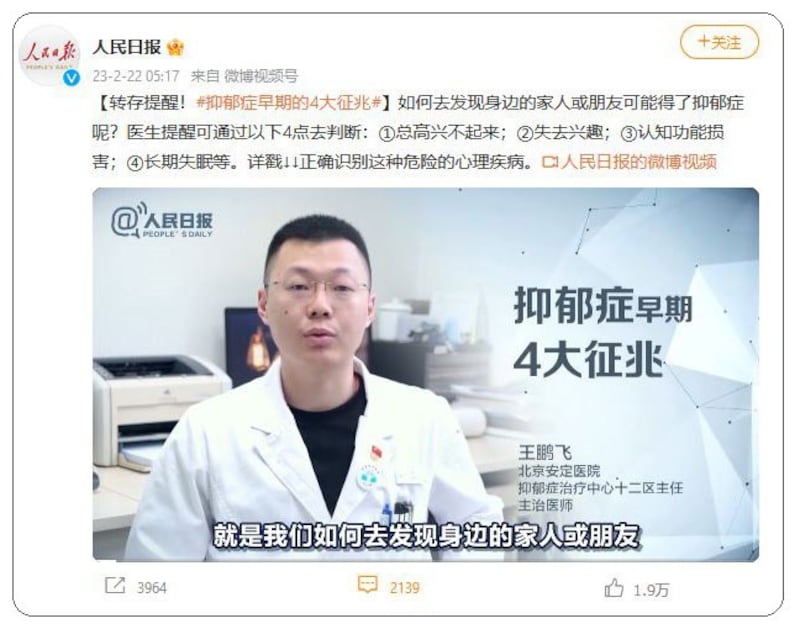
当理想碰上中国的现实
同样在高压的家庭环境成长的凯拉,长期面对政治冷漠的父母“像石头丢进深水中没有回应”,她也曾在高中时期提出关于民主的问题,而遭到老师当众嘲笑。当时她以为只要长大后就能替社会贡献一份力量。
“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改变,毕竟我也会慢慢长大,也会工作、会参加一些活动,然后再发现,现在连参加活动的权利都没有。我记得在初二之前,大部人的想法是将来要(海归)回国,去改变中国建设社会,然后你就发现,这个想法是假的,永远不是真的。”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就读博士的凯拉以英文名受访时说。
2018年,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,取消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,给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权利。凯拉是在那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帮助社会的理想终究无法实现,“政治性抑郁”逐渐将她吞噬,去年底看到彭立发在四通桥高挂横幅,眼泪终于控制不住。
“我记得(当时)是吃着吃着饭,眼泪就下来,然后就吃不了了。”凯拉苦笑,“就是在聊天谈,然后觉得心理控制不住,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,就是觉得好难受、好内疚、好抑郁。有时候不仅是情绪崩溃、哭啊之类的,还会过分地焦虑、担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美国执业心理谘商师梅尔(Shayna Mell)回复本台时说,政治抑郁症中出现的普遍感受确实包括绝望、无助和无力,以及类似悲伤的症状,那些经历过政治抑郁症的人,时常感到被困住,好像前途黯淡,让他们感到沮丧和精疲力竭。
在未点名特定国家的情况下,梅尔告诉记者:“威权政府可以通过严格审查和控制宣传内容,来加剧人们潜在的政治抑郁。 很多时候,容易患上政治抑郁症的人,会惊恐地看着自己自主行动的能力被剥夺,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程度的打压和限制。威权政府以这种破坏性方式行事,给人民留下了更大的恐惧、不确定性和绝望,让他们不确定是否能够再为自己做些什么。”
此外,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卢森(Robert Lusson)2017年在“赫芬顿邮报”(Huffpost)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,政治抑郁症可能是一种符合美国心理学会(APA)抑郁症标准的临床病症。
凯拉现在每周会与心理师进行一次谘商,内容涵盖她的生活细琐到国家大事,虽然政治并不是让她抑郁的唯一原因,但曾经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。她的另一半曾担心地问,要不要放下手机、停止看新闻?
“但你在抑郁的时候,反而更想看(新闻),想知道更多(社会上)发生的事情、别人是什么想的,像是一种强迫症的行为(obsessed behavior),等事件转个弯,有轻松的迹象时才会好一点。”凯拉形容抑郁时更想要刷新闻,除了追求心理的安全感,更是一种确认自己仍对社会事件有掌握。

白纸运动加深了政治抑郁
这些青年的“政治性抑郁”跟著中国疫情一起升温,从各地封城、强制方舱隔离、上海“四月之声”,加上习近平连任、徐州铁链女、贵州大巴等政治社会事件,越滚越烈,最后随著乌鲁木齐大火,以及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呼喊,一起爆发。
祈翠说,这个时候她意识到“政治性抑郁”是许多华人共同的痛苦。虽然众人起身反抗给了政治抑郁的青年们一丝慰藉,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、理想仍可实践,但中国政府的残暴压制,再次将他们推入政治抑郁的深渊。
本台此前报道,多名国内年轻人因为参与抗争遭到逮捕、失踪,身处海外的祈翠和凯拉在受访时不约而同地说,看著国内的同伴相继被抓,她们内疚感与无力感逐渐加重,仿佛一个无止尽的黑洞。
祈翠说:“白纸运动多多少少,是海外华人欠了墙内青年一个很大很大的人情,我们(海外)因此找到同伴,但实际上,国内年轻人的政治抑郁更严重,而且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。”

看似无止境的黑洞 希望在哪?
时代的一粒灰,落在这些理想青年头上,就是一座沉重的山,祈翠感觉这些政治、社会事件就像陨石一样,砸在中国年轻人身上,粉碎他们应该风光明媚的未来。尽管如此,祈翠最后不忘笑着向记者解释自己网名的由来,是拆字后暗示“祈习卒”。
这些政治抑郁的青年,也没有从此失去希望。
现在积极参与海外华人运动的凯拉相信,无论再微小、再遥远的声音都有力量,都是一种积累,有一天能够传回国内“愚公移山”。人在中国的张同学告诉本台,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政权更迭是必然会发生的,“我们朋友都想着,要保护好自己、保养好身体,我们要活着看到那一天,要放鞭炮呢。”
记者:陈品洁 责编:郑崇生 网编:洪伟
